 第371章 驕兵之計 我要做首輔
第371章 驕兵之計 我要做首輔
 第371章 驕兵之計 我要做首輔
第371章 驕兵之計 我要做首輔
兩千里的大運河,流的不只是碧綠的河水,更是帝國的血脈,南糧北運,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,無數綾羅綢緞,維持着京師達官顯貴的優沃生活,也維繫着天子守國門的豪言壯語。
圍繞着運河,形成了強大的利益集團,從沿岸的百姓,到形形色色的漕口幫會,再到運河衙門,士紳豪商,編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大網。
就像是月有陰晴圓缺,什麼都不可能長盛不衰。隨着運河維護成本越來越高,運力提升不上去,加上南北貨物運輸的需求成倍增加,不只是唐毅,還有很多人都看到了改變漕運的必要。
唐毅和這些人不同的地方,是他提出了解決的辦法,那就是維持現有運量不變,多出來的部分轉移到海運。
這個方案一下子就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,隨着整個開海的計劃推行,天津就成了門戶和試驗田。
就像任何改革都會觸動既得利益集團者,哪怕唐毅再小心,影響也是有的,而且還不小。
吳天成就給唐毅說道:「雖然運量規定不變,可這也只是漕糧的運量,至於南北往來的商船,朝廷可管不到。走運河雖然安全,可是速度奇慢,關卡林立,運費又高,大家早就苦不堪言。據我在江南的調查,有五成以上的商人希望走海運,直接從天津向京城發貨。官府的漕糧船隻不過是維持運河工人的生活而已,真正有油水的是商船,您說他們能不着急嗎?」
「還不止如此,眼下的天津三衛是鄰着運河建造的,如果開海之後,城區要擴建,碼頭那邊肯定繁榮起來,陸太保直接把碼頭的土地都給圈了起來,還大肆招募工人,徵用賬房書吏。原本指着運河吃飯的人都跑到港口去了。要我說陸太保就是在京城待久了,以為凡事只要有權力,一級壓着一級,就能把事情辦成了。可地方和京師不一樣,地方有豪強,有士紳,有幫會,有宗族。不把這些都弄明白了,貿然出手,肯定會遭到反噬的。」
唐毅呵呵一笑,「聽這話,你是很清楚了,給我說說,究竟有哪些勢力攙和進來,他們是不是鐵板一塊?」
吳天成連忙舉起了大拇指,讚嘆道:「師父就是一陣見血,實不相瞞。在四五年前,賣酒賣家具,咱們和沿線的商人就有往來,交通行建立之後,七爺和我們都下了一番苦功夫。按照您的吩咐,主要經營三條線,沿江,沿河,沿海。這運河上下,不敢說門清。也弄得七七八八。眼下在天津沖在前面的是聞香教,而聞香教還有三大助力。」
吳天成抓起水杯,潤潤喉嚨說道:「這第一股就是漕幫,他們以運河為生。擔心日後海運越來越發達,會把他們的飯碗子砸了,有聞香教挑唆,就跟着跳了起來。第二股就是天津當地的士紳,他們多數也都在運河周圍有產業,比如錢莊。客棧,貨倉一類的,海運興起,他們既擔心利益受損,又想吃海運的利益,跟着起鬨,也是待價而沽。」
唐毅點了點頭,他其實也有推測,只是沒有吳天成親身經歷,說的這麼明白。
「至於第三股,這個就麻煩點,主要是天津三衛的軍戶和世襲的將門。」吳天成說道:「本來開海對他們沒什麼壞處,可壞就壞在一些朝廷的大官身上。」
「怎麼回事?」唐毅好奇問道。
「是這樣的。天津開海的消息傳出來,有人就料定天津的地價會上漲,就有朝廷的達官貴人逼迫天津三衛的指揮使,指揮同知,指揮僉事,還有千戶百戶等人,把衛所的田產都轉給他們,甚至把軍戶變成佃農,替他們耕種。」吳天成譏誚地說道:「這幫大人也是當大爺當慣了,他們以為這些軍頭都是芝麻綠豆大的官,不值一提。可是別忘了,軍頭們都在天津生活了一兩百年,根基深厚,到處都是三親六故。而且這些年來,軍頭們已經把能吞的田都吞了,誰願意從自己身上割肉啊,這不,聞香教一煽動,他們也跟着鬧了起來。」
唐毅總算心中有數了,笑道:「天成,你說的頭頭是道,要是你又該如何處置?」
「我啊,當然……」吳天成把話吞了回去,憨笑道:「我哪懂啊,還是師父您運籌帷幄,弟子干點跑腿的活兒就成了!」
「哼,就會耍滑頭!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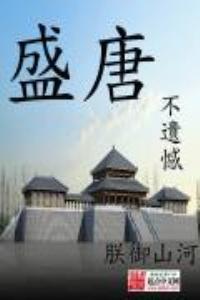 盛唐不遺憾 沒有屈辱和遺憾,只有勝利和輝煌。 鐵軌鋪向哪裡,大唐的利益就延伸到哪裡。 火炮戰車所向無敵,一帶一路再創輝煌。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盛唐不遺憾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
盛唐不遺憾 沒有屈辱和遺憾,只有勝利和輝煌。 鐵軌鋪向哪裡,大唐的利益就延伸到哪裡。 火炮戰車所向無敵,一帶一路再創輝煌。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盛唐不遺憾》還不錯的話請不要忘記向您QQ群和微博 超品相師 相師分九品,一品一重天 風水有境界,明理,養氣,修身,問道。 二十一世紀的一位普通青年偶獲諸葛亮生前的玄學傳承,沒有大志向的秦宇,只想守着老婆孩子熱炕頭,卻機緣巧合一步步走上相師之巔,成就
超品相師 相師分九品,一品一重天 風水有境界,明理,養氣,修身,問道。 二十一世紀的一位普通青年偶獲諸葛亮生前的玄學傳承,沒有大志向的秦宇,只想守着老婆孩子熱炕頭,卻機緣巧合一步步走上相師之巔,成就 大明最後一個狠人 魂穿越到大明最後一個皇太子朱慈烺的身上,以一個狠字貫穿一生。 殺建奴,滅流寇,斬貪官,開海禁,揚國威。 這個太子很兇殘,打仗比建奴還可怕,剿匪比流寇還折騰,摟銀子比貪官還徹底。 我大明,
大明最後一個狠人 魂穿越到大明最後一個皇太子朱慈烺的身上,以一個狠字貫穿一生。 殺建奴,滅流寇,斬貪官,開海禁,揚國威。 這個太子很兇殘,打仗比建奴還可怕,剿匪比流寇還折騰,摟銀子比貪官還徹底。 我大明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