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第135章 0130【令孤許的水利夢想】 北宋穿越指南
第135章 0130【令孤許的水利夢想】 北宋穿越指南
 第135章 0130【令孤許的水利夢想】 北宋穿越指南
第135章 0130【令孤許的水利夢想】 北宋穿越指南
試考時務策,俺的文章便是江壩水渠,州官們雖然頗為青睞,卻永遠不可能真正挖渠。」
「為何?」朱銘好奇道。
令孤許說:「江壩之地三四萬畝,兩面挨着漢江,一面挨着金沙河,取水卻極為困難。其實,想要修渠非常簡單,但須依託金沙湖修建堰壩,湖邊水田會被淹沒一些,被淹掉的全是王家水田。」
朱銘問道:「需要淹沒多少水田,又能灌溉多少旱田?」
令孤許說:「俺家請懂水利的先生來看過,只需淹沒王家數百畝水田,所修出來的堰壩和水渠,就能灌溉三萬多畝旱地。甚至,可以把一萬多畝旱地,改造為能種稻子的水田!」
「果然很難。」朱銘搖頭嘆息。
金沙湖周邊的數百畝水田,全是肥沃的上田,王家怎麼可能答應築壩?
說什麼水利修好之後,補償王家的損失,那全都是虛的,難免要出現扯皮和意外。
此處的水利,直至大明嘉靖年間,才由罷官歸鄉的水利專家李遇知,憑着自己極高的影響力來推動。
而且還是當時遭災,官府處理不了災民,李遇知說服官府以工代賑。但阻力還是太大,草草修了一段渠便作罷,僅能灌溉幾千畝地。
再下一次興修水利,就得等到新中國成立了,徹底解決那幾萬畝地的灌溉問題。
朱銘把此事記在心上,這關乎他未來的軍糧。
令孤許又說:「俺家的田產,大概占那裏的十二分之一,興修水利自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但還有無數鄉鄰可以得利啊,幾十年來,一直與王家溝通交涉,卻連半點法子也沒有。俺家甚至承諾,淹了王家多少地,等改造出水田之後,便補償他家多少地,再多贈送五十畝水田。還請知州作保簽訂契書,給足了誠意,王家根本不聽。」
朱銘只是笑笑,設身處地的想,如果他是王家人,也肯定不會答應,因為期間的變數太多。
必須靠武力強行推動!
令孤許繼續闡述家鄉改造計劃,他指着西邊說:「那邊也可興修水利,能灌溉數千畝地,與俺家沒有半點干係。但建造堰壩,同樣需要淹沒王家的良田,還要從王家的田地里經過。這王家的主宗和小宗,幾乎把金沙河的水源全部霸佔了。」
此時談這些沒用,朱銘問道:「令孤兄懂水利嗎?」
令孤許說:「學過,但都是自己胡亂看書,並無任何實際經驗。朱先生的數學,於水利一事大有裨益,俺也有認真在學。農為天下之本,水利又為農之本。哪天若能金榜題名,俺每到一地做官,必將當地的水利修好!」
朱銘又問:「你對當今朝廷怎麼看?」
令孤許說:「奸相誤國,不剷除朝中奸臣,社稷就難以振興。」
「為何朝堂奸臣眾多呢?」朱銘問道。
令孤許說:「官家被奸佞蒙蔽。」
朱銘忍不住發笑:「為何不是官家想做某些事情,那些奸臣只是投其所好呢?」
令孤許默然。
朱銘也不再說話,認認真真釣魚。
拉杆一看,餌料已被吃光。
令孤許也拉杆換餌,盯着浮標看了半天,忽然來一句:「若有昏君當道,就該從太子着手。」
朱銘撇撇嘴,那位太子,連他爹都不如。
「朱家哥哥,你這裏卻是涼爽。」鄭元儀扛着魚竿過來,還給朱銘帶了些小點心。
朱銘躺在青草里,用一片樹葉蓋住眼睛,遮擋光線開始打盹兒休息。
這日子,着實愜意。
鄭元儀坐在旁邊,將魚鈎拋入水中便不管,臉上帶着微笑看朱銘睡覺。
令孤許卻是有耐心的,靜靜盯着湖面,不多時便釣上一條草魚。
傍晚便在湖邊生火,僕人們忙來忙去,將魚獲打理乾淨還穿好竹枝,士子士女們架火烤魚便是。
又在洋州遊玩半月,還去拜謁了知州和通判。
等鄭家的商船,前往大明村裝運秋茶,朱銘、白崇彥才搭着順
 大明最後一個太子 崇禎十五年,松錦大戰以大明一方一敗塗地為結局落幕。至此,大明最後主力付之一炬。而秦俠這時卻好死不死穿越到明朝末代太子身上。歷史上,他是什麼結局?兩年後,李自成攻入京師,他成了亡國太子。三年後,
大明最後一個太子 崇禎十五年,松錦大戰以大明一方一敗塗地為結局落幕。至此,大明最後主力付之一炬。而秦俠這時卻好死不死穿越到明朝末代太子身上。歷史上,他是什麼結局?兩年後,李自成攻入京師,他成了亡國太子。三年後, 唐朝好地主 張超穿越武德四年,來到長安郊外灞上,成為了老府兵之子,但他卻只想做個悠閒的大唐好地主! 讀者群:656118488 (榮獲2016星創獎歷史優秀獎作品!)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唐朝
唐朝好地主 張超穿越武德四年,來到長安郊外灞上,成為了老府兵之子,但他卻只想做個悠閒的大唐好地主! 讀者群:656118488 (榮獲2016星創獎歷史優秀獎作品!)
各位書友要是覺得《唐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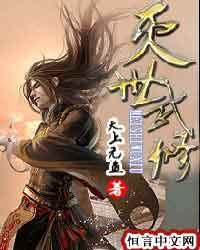 滅世武修 一條枷鎖,鏈住萬千星域。一顆心臟,沉浮黎明破曉。…………無數位面大陸,宗門林立,站在絕巔者,可笑蒼天,瞰大地。本是一代神體,卻得滅世傳承,是沉淪殺戮,還是走上巔峰之道?且看烏恆如何抉擇…………
滅世武修 一條枷鎖,鏈住萬千星域。一顆心臟,沉浮黎明破曉。…………無數位面大陸,宗門林立,站在絕巔者,可笑蒼天,瞰大地。本是一代神體,卻得滅世傳承,是沉淪殺戮,還是走上巔峰之道?且看烏恆如何抉擇…………